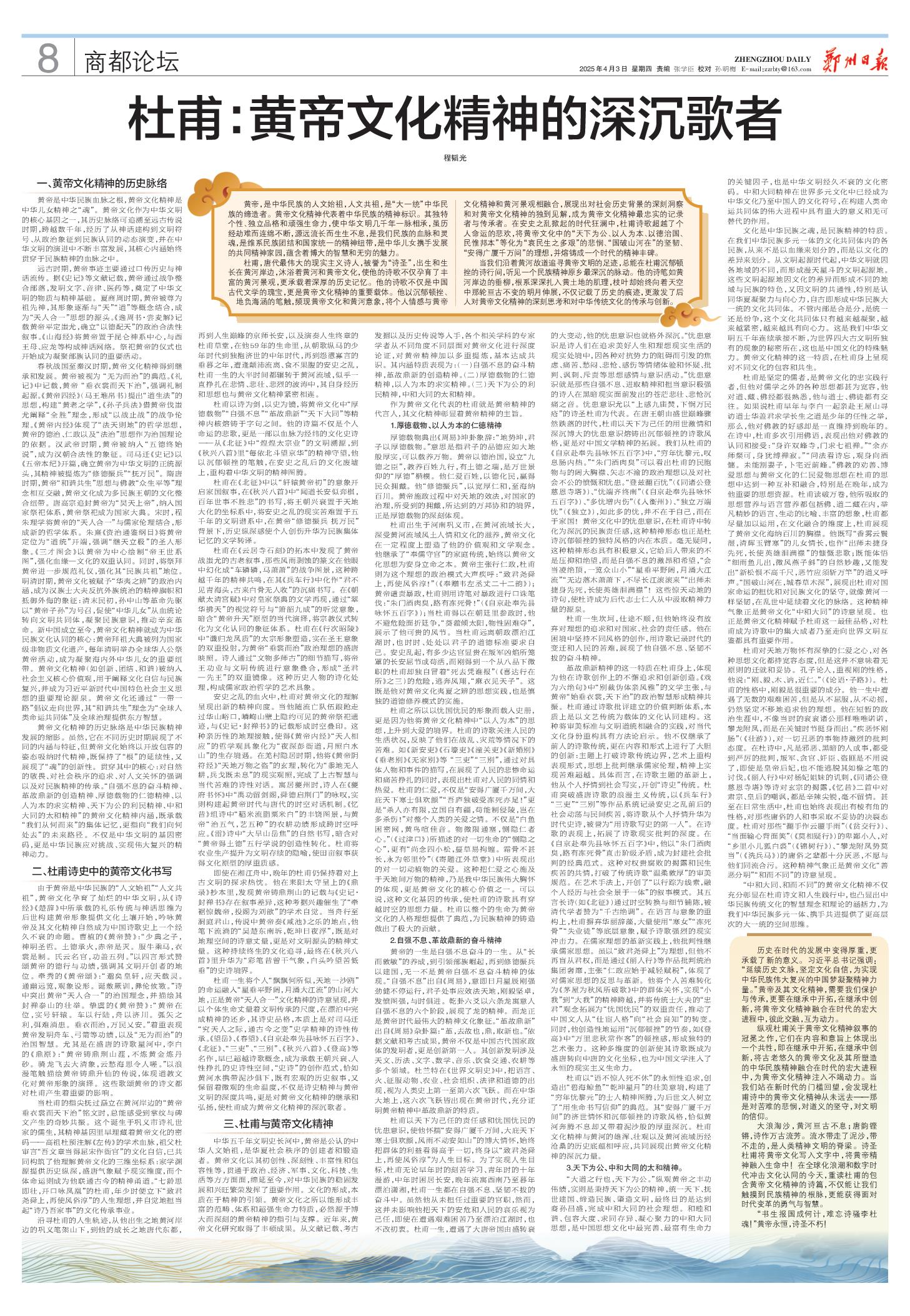程韬光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共祖,是“大一统”中华民族的缔造者。黄帝文化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独特个性、独立品格和顽强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几千年一脉相承,虽历经劫难而连绵不断,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携手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蕴含着博大的智慧和无穷的魅力。
杜甫,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出生和生长在黄河岸边,沐浴着黄河和黄帝文化,使他的诗歌不仅孕育了丰富的黄河景观,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他的诗歌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更是黄帝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他以沉郁顿挫、地负海涵的笔触,频现黄帝文化和黄河意象,将个人情感与黄帝文化精神和黄河景观相融合,展现出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刻洞察和对黄帝文化精神的独到见解,成为黄帝文化精神最忠实的记录者与传承者。在安史之乱掀起的时代狂澜中,杜甫诗歌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悲欢,将黄帝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民惟邦本”等化为“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国破山河在”的坚韧、“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并熔铸成一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当我们沿着黄河故道追寻黄帝文明的足迹,总能在杜甫沉郁顿挫的诗行间,听见一个民族精神原乡最深沉的脉动。他的诗笔如黄河岸边的垂柳,根系深深扎入黄土地的肌理,枝叶却始终向着天空中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伸展,不仅记载了历史的痕迹,更激发了后人对黄帝文化精神的深刻思考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黄帝文化精神的历史脉络
黄帝是中华民族血脉之根,黄帝文化精神是中华儿女精神之“魂”。黄帝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之一,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远古传说时期,跨越数千年,经历了从神话建构到文明符号、从政治象征到民族认同的动态演变,并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其核心内涵始终贯穿于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
远古时期,黄帝事迹主要通过口传历史与神话流传。据《史记》等文献记载,黄帝通过战争整合部落,发明文字、音律、医药等,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夏商周时期,黄帝被尊为祖先神,其形象逐渐与“天”“道”等概念结合,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逸周书·尝麦解》记载黄帝平定蚩尤,确立“以德配天”的政治合法性叙事。《山海经》将黄帝置于昆仑神系中心,与西王母、应龙等构成神话网络。祭祀黄帝的仪式也开始成为凝聚部族认同的重要活动。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文化精神得到继承和发展。黄帝被视为 “无为而治”的典范。《礼记》中记载,黄帝 “垂衣裳而天下治”,强调礼制起源。《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提出“道生法”的思想,构建“黄老之学”,《孙子兵法》借黄帝伐蚩尤阐释“全胜”理念,形成“以战止战”的战争伦理。《黄帝内经》体现了“法天则地”的哲学思想,黄帝的德治、仁政以及“法治”思想作为治国理论的依据。汉武帝时期,黄帝被纳入“五德终始说”,成为汉朝合法性的象征。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确立黄帝为中华文明的正统源头,其精神被提炼为“修德振兵”“抚万民”。隋唐时期,黄帝“和谐共生”思想与佛教“众生平等”理念相互交融,黄帝文化成为多民族王朝的文化整合纽带。唐高宗追封黄帝为“昊天上帝”,纳入国家祭祀体系,黄帝祭祀成为国家大典。宋时,程朱理学将黄帝的“天人合一”与儒家伦理结合,形成新的哲学体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将黄帝定位为“道统”开端,强调“继天立极”的圣人形象。《三才图会》以黄帝为中心绘制“帝王世系图”,强化血缘—文化的双重认同。同时,将祭拜黄帝进一步规范礼仪,强化其“民族共祖”地位。明清时期,黄帝文化被赋予“华夷之辨”的政治内涵,成为汉族士大夫反抗外族统治的精神旗帜和抵御外侮的象征:清末民初,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以“黄帝子孙”为号召,促使“中华儿女”从血统论转向文明共同体,凝聚民族意识,推动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至今,黄帝文化精神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黄帝拜祖大典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清明举办全球华人公祭黄帝活动,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黄帝文化精神(如创新、团结、和谐)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于阐释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黄帝文化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向世界,其“和谐共生”理念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黄帝文化精神的历史脉络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缩影。虽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了不同的内涵与特征,但黄帝文化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时代精神,既保持了“根”的延续性,又展现了“魂”的创新性。贯穿其中的核心:对自然的敬畏、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对人文关怀的强调以及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厚德载物的仁德精神、以人为本的求实精神、天下为公的利民精神、中和大同的太和精神”的黄帝文化精神内涵,既承载“我们从何而来”的集体记忆,更指向“我们向何处去”的未来路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更是中华民族应对挑战、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二、杜甫诗史中的黄帝文化书写
由于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共祖”,黄帝文化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诗经》《楚辞》中?所承载的礼乐传统与神话思维为后世构建黄帝形象提供文化土壤开始,吟咏黄帝及其文化精神自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曹植的《黄帝赞》:“少典之子,神明圣哲。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盖五列。”?以四言形式赞颂黄帝的德行与功绩,强调其文明开创者的地位。?牵秀的《黄帝颂》:?“邈矣皇轩,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斁。”?诗中突出黄帝“天人合一”的治国理念,并描绘其封禅泰山的壮举。?挚虞的《黄帝赞》:?“黄帝在位,实号轩辕。车以行陆,舟以济川。弧矢之利,弭难消患。垂衣而治,万民乂安。”?着重表现黄帝发明舟车、弓箭等功绩,以及“无为而治”的治国智慧。尤其是在盛唐的诗歌星河中,?李白的《鼎原》:?“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大清象,云愁海思令人嗟。”?以浪漫笔触描绘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体现道教文化对黄帝形象的演绎。这些歌颂黄帝的诗文都对杜甫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当杜甫的指尖抚过矗立在黄河岸边的“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铭文时,总能感受到掌纹与碑文产生的奇妙共振。这个诞生于巩义市诗礼世家的儒生,其精神基因里早埋藏着黄帝文化的密码——高祖杜预注解《左传》的学术血脉,祖父杜审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文化自信,已共同构筑了他理解黄帝文化的三维坐标系:家学渊源提供历史纵深,盛唐气象赋予现实维度,而个体命运则成为他联通古今的精神甬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年少时便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并自觉地担当起“诗乃吾家事”的文化传承事业。
沿寻杜甫的人生轨迹,从他出生之地黄河岸边的巩义笔架山下,到他的成长之地唐代东都,再到人生巅峰的京师长安,以及演奏人生终章的杜甫草堂,在他59年的生命里,从朝歌纵马的少年时代到独抱济世的中年时代,再到怨懑寡言的垂暮之年,遭逢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安史之乱,杜甫一生的大半时间都辗转于黄河流域,似乎一直挣扎在悲情、悲壮、悲烈的波涛中,其自身经历和思想也与黄帝文化精神紧密相连。
杜甫以诗为剑,以史为镜,将黄帝文化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天下大同”等精神内核熔铸于字句之间。他的诗篇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一部以血脉为经纬的文化史诗——从《北征》中“煌煌太宗业”的文明溯源,到《秋兴八首》里“每依北斗望京华”的精神守望,他以沉郁顿挫的笔触,在安史之乱后的文化废墟上,重构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
杜甫在《北征》中以“轩辕黄帝初”的意象开启家国叙事,在《秋兴八首》中“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的书写,将王朝兴衰置于天地大化的坐标系中,将安史之乱的现实苦难置于五千年的文明谱系中,在黄帝“修德振兵 抚万民”背景下,历史纵深感使个人创伤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转译。
杜甫在《云居寺石刻》的拓本中发现了黄帝战蚩尤的古老叙事,那些风雨剥蚀的篆文在他眼中幻化成“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图景,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在其《兵车行》中化作“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沉痛书写。在《朝献太清宫赋》中对皇家祭典的文学再现,通过“翠华拂天”的视觉符号与“箫韶九成”的听觉意象,暗含“黄帝升天”原型的当代演绎,将宗教仪式转化为文化认同的象征体系。杜甫在《行次昭陵》中“谶归龙凤质”的太宗形象塑造,实在圣王意象的双重投射,为黄帝“垂裳而治”政治理想的盛唐映照。诗人通过“文物多师古”的细节描写,将帝王功业与文明传统进行意象叠合,形成“圣君—先王”的双重镜像。这种历史人物的诗化处理,构成儒家政治哲学的艺术具象。
安史之乱的血火中,杜甫对黄帝文化的理解呈现出新的精神向度。当他随流亡队伍踉跄走过华山峪口,嶙峋山壁上隐约可见的黄帝祭祀遗迹,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形成时空叠印。这种亲历性的地理接触,使得《黄帝内经》“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具象化为“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的生存境遇。在羌村隐居时期,他将《黄帝阴符经》“天地万物之盗”的玄理,转化为“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的现实观照,完成了上古智慧与当代苦难的诗性对话。寓居夔州时,诗人在《夔府书怀》中“禹功留剑阁,舜德启荆门”的咏叹,实则构建起黄帝时代与唐代的时空对话机制。《忆昔》组诗中“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饶图景,与黄帝“治五气,艺五种”的农耕功绩形成跨时空呼应。《雷》诗中“大旱山岳焦”的自然书写,暗含对“黄帝得土德”五行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杜甫将农业生产提升为文明存续的隐喻,使田亩叙事获得文化原型的厚重质感。
即使在湘江舟中,晚年的杜甫仍保持着对上古文明的探求热忱。他在耒阳太守呈上的《鼎录》抄本里,发现黄帝铸鼎荆山的记载与《史记·封禅书》存在叙事差异,这种考据兴趣催生了“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的学术自觉。当舟行至洞庭君山,传说中黄帝奏《咸池》之乐的地点,他笔下流淌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既是对地理空间的诗意丈量,更是对文明源头的精神丈量。这种持续终生的文化追寻,最终在《秋兴八首》里升华为“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的史诗境界。
杜甫一生将个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命运融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山河大地,正是黄帝“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诗意呈现,并以个体生命丈量着文明传承的尺度,在漂泊中完成精神的还乡,其诗史品格,本质上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精神的诗性传承。《望岳》、《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登高》等名作,早已超越诗歌概念,成为承载王朝兴衰、人性挣扎的史诗性空间,“史诗”的创作范式,恰如黄河水携带泥沙俱下,既有宏观的历史叙事,又保留着微观的生命温度,不仅是诗史精神与黄帝文明的深度共鸣,更是对黄帝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使杜甫成为黄帝文化精神的深沉歌者。
三、杜甫与黄帝文化精神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河中,黄帝是公认的中华人文始祖,是华夏社会秩序的创建者和锻造者。黄帝文化以其初创性、深刻性、丰富性和包容性等,贯通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活等方方面面,绵延至今,对中华民族的稳固发展和兴旺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的形成,本质在于精神的引领。黄帝文化之所以能形成丰富的范畴、体系和超强生命力特质,必然源于博大而深刻的黄帝精神的指引与支撑。近年来,黄帝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历史传说等入手,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黄帝文化进行深度论证,对黄帝精神加以多重提炼,基本达成共识。其内涵特质表现为:(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二)厚德载物的仁德精神,以人为本的求实精神。(三)天下为公的利民精神,中和大同的太和精神。
作为黄帝文化代表的杜甫就是黄帝精神的代言人,其文化精神彰显着黄帝精神的主旨。
1.厚德载物、以人为本的仁德精神
厚德载物典出《周易》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指君子的品德应如大地般厚实,可以载养万物。黄帝以德治国,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有土德之瑞,是万世景仰的“厚德”楷模。他仁爱百姓,以德化民,赢得民众拥戴。他“修德振兵”,以宽厚仁和,至海纳百川。黄帝施政过程中对天地的效法,对国家的治理,所受到的拥戴,所达到的万邦协和的境界,正是厚德载物的深刻体现。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市,在黄河流域长大,深受黄河流域风土人情和文化的滋养,黄帝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念。他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始终以黄帝文化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黄帝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黄帝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展示了他可贵的风节。当杜甫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达官显贵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危险,逃奔风翔,“麻衣见天子”。这既是他对黄帝文化夷夏之辨的思想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杜甫之所以以忧国忧民的形象而载入史册,更是因为他将黄帝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上升到大爱的境界。杜甫的诗歌关注人民的生活状况,反映了他们在战乱、灾荒等情况下的苦难。如《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 “三吏”“三别”,通过对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在展现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痛苦挣扎的同时,表现出杜甫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杜甫的仁爱,不仅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更是“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情。不仅是“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所描述的对一切生命的“恻隐之心”,更有“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中所表现出的对一切动植物的关爱。这种把仁爱之心施及于天地间万物的精神,乃是我中华民族伟大胸怀的体现,更是黄帝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可以说,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使杜甫的诗歌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力量。杜甫以整个的生命为黄帝文化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为民族精神的铸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奋斗精神
黄帝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奋斗的一生。从“长而敦敏”的养成,到引领部族崛起,再到修德振兵以建国,无一不是黄帝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体现。“自强不息”出自《周易》,意即日月星辰刚强劲健不停运行,君子处事应效法天地,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与时俱进。乾卦六爻以六条龙寓意人自强不息的六个阶段,展现了龙的精神。而龙正是黄帝时代最伟大的精神文化象征。“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篇:“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依据文献和考古成果,黄帝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发明者,更是创新第一人。其创新发明涉及天文、历法、文字、数学、音乐、饮食交通、农耕等多个领域。杜兰特在《世界文明史》中,把语言、火、征服动物、农业、社会组织、法律和道德的出现,视为人类史上第一至第六次飞跃。而在中华大地上,这六次飞跃皆出现在黄帝时代,充分证明黄帝精神中革故鼎新的特质。
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使他怀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博大情怀,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终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人生目标。为了实现人生目标,杜甫无论早年时的刻苦学习、青年时的十年漫游,中年时困居长安,晚年流寓西南乃至暮年漂泊潇湘,杜甫一生都在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中。虽然他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杜甫一生,遭遇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大变动,他的忧患意识也就格外深沉。“忧患意识是诗人们在追求美好人生和理想现实生活的现实处境中,因各种对抗势力的阻碍而引发的焦虑、痛苦、愁闷、悲怆、感伤等情绪体验和怀疑、批判、讽刺、斥责等思想感情与意识活动。”忧患意识就是那些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极强的诗人在黑暗现实面前发出的苍茫悲壮、悲怆沉痛之音。忧患意识尤以“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的诗圣杜甫为代表。在唐王朝由盛世巅峰骤然跌落的时代,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激情和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熔铸出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更是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拓展。我们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可以看出杜甫的民胞物与的阔大胸襟、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忧患。“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忧”(《独立》),如此多的忧,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家国!黄帝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在杜甫诗中转化为深沉的民族责任感,这种精神形态也正是杜诗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的内在本质。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形态具有积极意义,它给后人带来的不是压抑和绝望,而是自强不息的激昂和希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些惊天动地的诗句,使杜诗成为后代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杜甫一生坎坷,仕途不顺,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他在困境中坚持不同风格的创作,用诗歌记录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苦难,展现了他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革故鼎新精神的这一特质在杜甫身上,体现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追求和创新创造。《戏为六绝句》中“别裁伪体亲风雅”的文学主张,与黄帝“始垂衣裳,天下治”的政治智慧形成精神共振。杜甫通过诗歌批评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本质上是以文艺传统为载体的文化认同建构。这种将审美标准与文明道统相融合的实践,对当代文化身份重构具有方法论启示。他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诗歌传统,更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主题上打破诗歌传统边界,艺术上重构表现形式,思想上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精神上实现苦难超越?。具体而言,在诗歌主题的革新上,他从个人抒情到社会写实,?开创“诗史”传统。?杜甫突破盛唐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系统记录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荡与民间疾苦,将诗歌从个人抒情升华为时代史诗,被誉为“用诗歌写史的第一人”?。在诗歌的表现上,拓展了诗歌现实批判的深度。?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击阶级矛盾,成为封建社会批判的经典范式。这种对权贵腐败的揭露和民生疾苦的共情,打破了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审美规范?。在艺术手法上,开创了“以行踪为线索,融个人经历与社会全景于一体”的叙事模式。其五言长诗(如《北征》)通过时空转换与细节铺陈,被清代学者赞为“千古绝调”?。在?语言与意象的重构上,?杜甫摒弃华丽辞藻,大量使用“寒女”“冻死骨”“失业徒”等底层意象,赋予诗歌强烈的现实冲击力。在儒家理想的革新实践上,他?批判性继承儒家思想。?虽以“致君尧舜上”为理想,但他不再盲从君权,而是通过《丽人行》等作品批判统治集团奢靡,主张“仁政应始于减轻赋税”,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反思与革新?。他将个人苦难转化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体关怀,实现“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跨越,并将传统士大夫的“忠君”观念拓展为“忧国忧民”的双重责任,推动了中国文人从“仕宦人格”向“社会良知”的转变?。同时,他创造性地运用“沉郁顿挫”的节奏,如《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的顿挫感,形成独特的艺术张力?。这种多维度的创新使其诗歌既成为盛唐转向中唐的文化坐标,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永恒的现实主义生命力。
杜甫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永恒性追求,创造出“碧海鲸鱼”“乾坤星月”的壮美意境,?构建了“穷年忧黎元”的士人精神图腾,为后世文人树立了“用生命书写信仰”的典范?。其“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济世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恰似黄河奔腾不息却又带着泥沙般的厚重深沉。杜甫文化精神与黄河的雄浑、壮观以及黄河流域历经沧桑的历史底蕴相呼应,共同展现出黄帝文化精神的深沉力量。
3.天下为公、中和大同的太和精神。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纵观黄帝之丰功伟绩,实则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精神,统一天下、抚世建国、缔造民族、肇造文明,最终目的是达到裔孙昌盛,完成中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和睦和谐、包容大度、求同存异、凝心聚力的中和大同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关键因子,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文化密码。中和大同精神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文化符号,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的特质。在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内的各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来划分的,而是以文化的差异来划分。从文明起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各地域的不同,而形成漫天星斗的文明起源地。这些文明起源地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地域与民族的特色,又因文明的共通性,特别是认同华夏凝聚力与向心力,自古即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不管内部是合是分,是统一还是纷争,这个文化共同体只有越来越凝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具有向心力。这是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承接不断,为世界四大古文明所独有的现象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黄帝文化精神的这一特质,在杜甫身上呈现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共生。
杜甫是坚定的儒者,是黄帝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在诗中,杜甫多次引用佛语,表现出他对佛教的认同和接受:“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问法看诗忘,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佛教的劝善、博爱思想与黄帝文化的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的思想中达到一种互补和融合,特别是在晚年,成为他重要的思想资源。杜甫读破万卷,他所吸取的思想营养与语言营养都包括佛、道二藏在内,举凡精妙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杜甫都尽量加以运用,在文化融合的维度上,杜甫展现了黄帝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既写“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的儿女情长,也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慷慨悲歌;既能体悟“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自然妙趣,又能发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道义呼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展现出杜甫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就像黄河一样坚韧,在乱世中延续着文化的脉络。这种精神气象正是黄帝文化“中和大同”的诗意呈现。也正是黄帝文化精神赋予杜甫这一最佳品格,对杜甫成为诗歌中的集大成者乃至走向世界文明互鉴都具有重要作用。
杜甫对天地万物怀有深挚的仁爱之心,对各种思想文化都持宽容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孔子论人,重视刚的性格,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杜甫的性格中,刚毅是很重要的成分。他一生中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是从不屈服,从不动摇,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他的理想。他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不像当时的衮衮诸公那样唯唯诺诺,攀龙附凤,而是在关键时节挺身而出。“疾恶怀刚肠”(《壮游》),对一切丑恶的事物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杜诗中,凡是邪恶、黑暗的人或事,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叛军、贪官、奸臣、盗匪是不用说了,即使是皇帝后妃,也不能逃脱其如椽之笔的讨伐。《丽人行》中对杨妃姐妹的讥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对玄宗的揭露,《忆昔》二首中对肃宗、皇后的嘲讽,都是辛辣尖锐,毫不留情。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杜甫也始终表现出有棱有角的性格,对那些庸俗的人和事采取不妥协的决裂态度。杜甫对那些“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的卑鄙小人,对“乡里小儿狐白裘”(《锦树行》)、“攀龙附凤势莫当”(《洗兵马》)的庸俗之辈都十分厌恶,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这种精神气象正是黄帝文化“善恶分明”“和而不同”的诗意呈现。
“中和大同、和而不同”的黄帝文化精神不仅充分彰显在杜甫诗文和人生践行中,也凸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理念和理论的涵括力,为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携手共进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大一统的空间思维。
历史在时代的发展中变得厚重,更承载了新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帝及其文化精神,需要我们保护与传承,更要在继承中开拓,在继承中创新,将黄帝文化精神融合在时代的宏大进程中,彼此交融,互为动力。
纵观杜甫关于黄帝文化精神叙事的冠冕之作,它们在内容和意旨上体现出一个共性,即在继承中开拓,在继承中创新,将古老悠久的黄帝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精神融合在时代的宏大进程中,为黄帝文化精神注入不竭动力。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回望,会发现杜甫诗中的黄帝文化精神从未远去——那是对苦难的悲悯,对道义的坚守,对文明的信仰。
大浪淘沙,黄河亘古不息;唐韵铿锵,诗作万古流芳。流水带走了泥沙,带不走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脊梁。诗圣杜甫将黄帝文化写入文字中,将黄帝精神融入生命中!在全球化浪潮和数字时代冲击文化认同的今天,重读杜甫的包含黄帝文化精神的诗篇,不仅能让我们触摸到民族精神的根脉,更能获得面对时代变革的勇气与智慧。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黄帝永恒,诗圣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