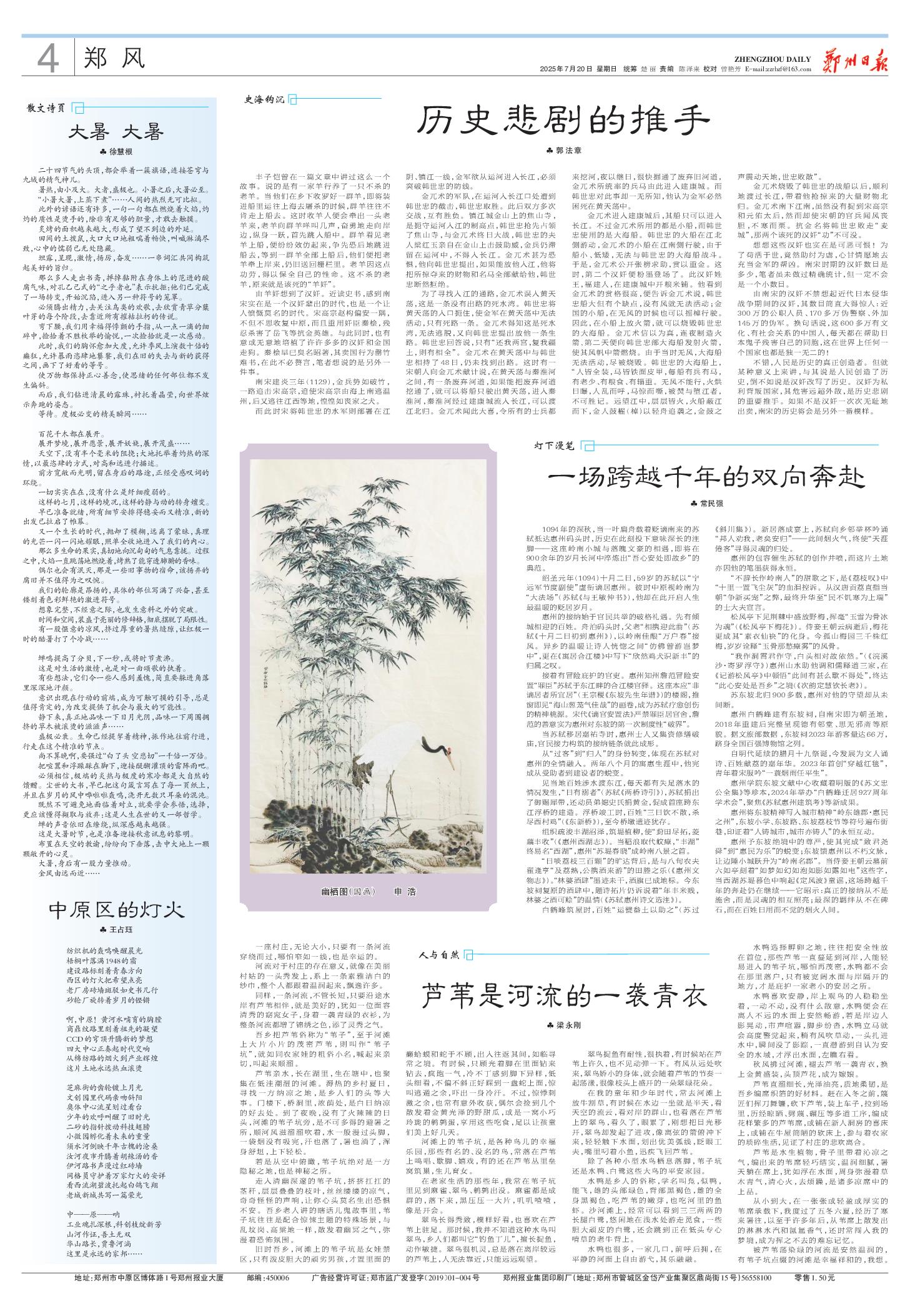? 梁永刚
一座村庄,无论大小,只要有一条河流穿绕而过,哪怕窄如一线,也是幸运的。
河流对于村庄的存在意义,就像在美丽村姑的一头秀发上,系上一条素雅洁白的纱巾,整个人都跟着温润起来,飘逸许多。
同样,一条河流,不管长短,只要沿途水岸有芦苇相伴,就是美好的,犹如一位面容清秀的窈窕女子,身着一袭青绿的衣衫,为整条河流都增了锦绣之色,添了灵秀之气。
吾乡把芦苇俗称为“苇子”,至于河滩上大片小片的茂密芦苇,则叫作“苇子坑”,就如同农家娃的粗俗小名,喊起来亲切,叫起来顺溜。
芦苇亲水,长在湖里,生在塘中,也聚集在低洼潮湿的河滩。溽热的乡村夏日,寻找一方纳凉之地,是乡人们的头等大事。门楼下,桥洞里,浓荫处,是白日纳凉的好去处。到了夜晚,没有了火辣辣的日头,河滩的苇子坑旁,是不可多得的避暑之所,顺河风滋溜溜吹着,水一般漫过头脚,一袋烟没有吸完,汗也落了,暑也消了,浑身舒坦,上下轻松。
若是从空中俯瞰,苇子坑绝对是一方隐秘之地,也是神秘之所。
走入清幽深邃的苇子坑,挤挤扛扛的茎秆,层层叠叠的枝叶,丝丝缕缕的凉气,奇奇怪怪的声响,让你心头莫名生出恐惧不安。吾乡老人讲的瞎话儿鬼故事里,苇子坑往往是配合惊悚主题的特殊场景,与乱坟岗、高粱地一样,散发着幽冥之气,弥漫着恐怖氛围。
旧时吾乡,河滩上的苇子坑是女娃禁区,只有泼皮胆大的顽劣男孩,才置里面的癞蛤蟆和蛇于不顾,出入往返其间,如临寻常之境。有时候,只顾光着脚在里面钻来钻去,疯跑一气,冷不丁感到脚下异样,低头细看,不偏不斜正好踩到一盘蛇上面,惊叫逃遁之余,吓出一身冷汗。不过,惊悸刺激之余,也常有意外收获,偶尔会捡到几个散发着金黄光泽的野甜瓜,或是一窝小巧玲珑的鹌鹑蛋,享用这些吃食,足以让孩童们美上好几天。
河滩上的苇子坑,是各种鸟儿的幸福乐园,那些有名的、没名的鸟,常落在芦苇上鸣唱、歇脚、嬉戏,有的还在芦苇丛里垒窝筑巢,生儿育女。
在老家生活的那些年,我常在苇子坑里见到麻雀、翠鸟、鹌鹑出没。麻雀都是成群的,落下来,黑压压一大片,叽叽喳喳,像是开会。
翠鸟长得秀致,模样好看,也喜欢在芦苇上驻足。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水鸟叫翠鸟,乡人们都叫它“钓鱼丁儿”,擅长捉鱼,动作敏捷。翠鸟很机灵,总是落在离岸较远的芦苇上,人无法靠近,只能远远观望。
翠鸟捉鱼有耐性,很执着,有时候站在芦苇上许久,也不见动弹一下。有风从远处吹来,翠鸟娇小的身体,就会随着芦苇的节奏一起荡漾,很像枝头上盛开的一朵翠绿花朵。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常去河滩上放牛割草,有时候在水边一坐就是半天,看天空的流云,看对岸的群山,也看落在芦苇上的翠鸟,看久了,眼累了,刚想把目光移开,翠鸟却发起了进攻,像离弦的箭俯冲下来,轻轻触下水面,划出优美弧线,眨眼工夫,嘴里叼着小鱼,迅疾飞回芦苇。
除了各种小型水鸟栖息落脚,苇子坑还是水鸭、白鹭这些大鸟的平安家园。
水鸭是乡人的俗称,学名叫凫,似鸭,能飞,雄的头部绿色,背部黑褐色,雌的全身黑褐色,吃芦苇的嫩芽,也吃河里的鱼虾。沙河滩上,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长腿白鹭,悠闲地在浅水处游走觅食,一些胆大顽皮的白鹭,还会跳到正在低头专心啃草的老牛背上。
水鸭也很多,一家几口,前呼后拥,在平静的河面上自由游弋,其乐融融。
水鸭选择孵卵之地,往往把安全性放在首位,那些芦苇一直蔓延到河岸,人能轻易进入的苇子坑,哪怕再茂密,水鸭都不会在那里落户,只有被宽阔水面与岸隔开的地方,才是庇护一家老小的安居之所。
水鸭喜欢安静,岸上观鸟的人稳稳坐着,一动不动,没有什么敌意,水鸭便会在离人不远的水面上安然畅游,若是岸边人影晃动,市声喧嚣,脚步纷沓,水鸭立马就会高度警觉起来,稍有风吹草动,一头扎进水中,瞬间没了影踪,一直潜游到自认为安全的水域,才浮出水面,左瞧右看。
秋风拂过河滩,褪去芦苇一袭青衣,换上金黄盛装,头顶芦花,成为嫁娘。
芦苇直溜细长,光泽油亮,质地柔韧,是吾乡编席织箔的好材料。赶在入冬之前,篾匠们挥刀舞镰,砍下芦苇,装上车子,拉到场里,历经晾晒、劈蔑、碾压等多道工序,编成花样繁多的芦苇席,或铺在新人洞房的喜床上,或铺在牛屋简陋的软床上,参与着农家的琐碎生活,见证了村庄的悲欢离合。
芦苇是水生植物,骨子里带着沁凉之气,编出来的苇席轻巧结实,温润细腻,暑天躺在席上,犹如浮在水面,周身弥漫着草木青气,清心火,去烦躁,是诸多凉席中的上品。
从小到大,在一张张或轻盈或厚实的苇席承载下,我度过了五冬六夏,经历了寒来暑往,以至于许多年后,从苇席上散发出的淋淋水汽和氤氲香气,还时常闯入我的梦境,成为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
被芦苇荡染绿的河流是安然温润的,有苇子坑点缀的河滩是幸福祥和的,我想。